古人是怎樣處理公文的?
發布日期:2017-08-29 14:35 信息來源: 訪問量:? 字體 :[ 大 ][ 中 ][ 小 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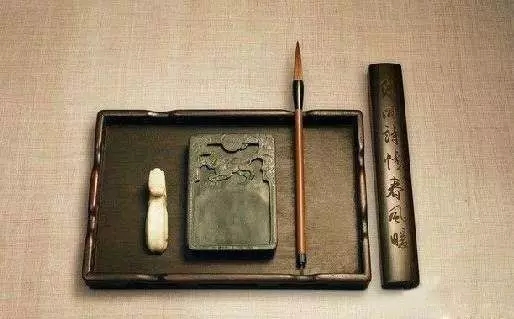
我國歷史上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文書工作制度,有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。
文書正副本制度
重要公文須建立副本,這一制度自西周時即已形成。王命文書頒發之后,正本交受命者,副本交由內史保存。中央各官署的文件,一份在原官署存檔,一份上納王室“天府”文件庫保存。地方官署的重要文書也是一式兩份,一份自行保存,另一份送交所屬諸州史收存。
文書正副本制度,既是文書工作的一項重要制度,也是檔案工作的一項重要制度,為現行公文的執行和歷史文件的保存提供了保證。
公文主官簽發制度(判署簽押制度)
公文須由主官簽名或畫押后才能生效,現代文書學稱之為“簽發”,古代稱之為“判署簽押”。這一制度由文書制作者(史官)簽名逐步發展而形成。
戰國時期,齊國國相田嬰首先在契券文書上簽名,稱為“押券”,各官署仿行之,在官文書(限于縑帛書寫的公文,簡牘文書則多用封泥)上押署。經過秦漢的發展,到三國時公文簽押制度已正式形成。東晉以后正式以紙書寫公文,在紙上便于押署,公文押署制度即被朝廷定制下來。
請示類公文一文一事制度
一文一事,即一件公文只陳述一件事,不同的事不得混雜在一件公文中。這種做法大約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,通用于唐代,而見諸典籍記載的成文制度則是在宋代。南宋《慶元條法事類·卷十六·文書門》規定:“諫奏公事,皆直述事狀,若名件不同,應分送所屬,而非一宗事者,不得同為一狀。”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關于一文一事制度的最早記錄。
請示類公文實行一文一事制度,符合文書工作的發展規律,因為它能突出公文內容主旨,加快行文速度,提高公文處理的效率,也便于公文的管理、查詢和文書檔案的保管,所以一直沿用至今。
“引黃”“貼黃”制度
“貼黃”一詞源于唐代,唐代敕書用黃紙書寫,如需作局部改動,就用黃紙貼上改寫,稱為“貼黃”。到了宋代,“貼黃”的概念有所變化:凡上行文書寫完后如有重要補充說明,可另外寫于黃紙上貼于正文后,稱為“貼黃”。
宋代規定,凡送呈朝廷的章奏文書,須將內容要點、呈遞日月寫于黃紙上,貼于封皮或文首,稱為“引黃”。“引黃”是公文摘由的開始,它能使受理公文者一目了然地看到公文的主要內容,從而提高了公文處理的效率。
明清兩代,“貼黃”一詞的意義又有變化。崇禎即位之初,批閱章奏時深感文字之冗繁,便命內閣制作“貼黃”式樣,令進本官員自己將疏奏用百字左右進行摘要,貼附于文尾,以便皇帝閱覽。此種“貼黃”,實際上是宋代“引黃”制的發展。
用現代文書學的觀點看,宋代的“引黃”和明清的“貼黃”,實際上就是公文摘由制度。現代制作篇幅較長的公文也附內容摘要(或摘由),就是對古代文書“貼黃”“引黃”制度的繼承和發展。
公文收發、辦理的登記制度
發出公文或收到公文要進行詳細登記,這一制度在秦代之前就已經初見端倪。傳送或收到文書,必須登記發文或收文的月日朝夕,以便及時回復。
到了宋代,公文登記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:公文收發不僅要登記,而且重要的涉及機密的公文還要裝入封皮折角密封,并逐一編號。編號的目的是為了更嚴格地登記,有利于加強登記人員的責任心,并便于根據登記來承辦和催辦。
元代對公文處理的程序是:收到公文后先登記,注明日期,然后發放給有關部門辦理,承辦人員要簽字接案,處理完畢后歸檔。元代還建立了“朱銷文簿”,即將應辦公文逐一登記,辦完結案后再依次勾銷,并簡要注明辦理情況。
清代衙署對公文已經實行分類登記,根據公文的發文衙署和公文性質,實行分簿登記,這是文書工作走向成熟的標志。
公文票擬(擬辦)制度
票擬,即由秘書部門首先對題奏文書進行閱讀,并在一張專用紙簽上擬出初步處理意見,然后再轉呈皇帝定奪,這種做法類似于今天由辦公室主任在公文處理單上寫上“擬辦意見”。票擬制形成于明代宣德年間,當時內閣職能日顯重要,“凡中外奏章,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,謂之條旨”。即閣臣將匯集于內閣的各種奏章預先列出處置意見,貼于章奏上進呈皇帝裁決。
票擬本來只是自然形成的題奏處理程序,明英宗登基時,因為只有9歲而由太后執政,太后怕擔擅權之名,就命令內閣對所有題奏本章先提出初步意見,再連同原來的題奏送太后定奪。從此票擬就成為一項公文處理的制度。票擬制度有利于發揮秘書部門的參謀作用,是秘書工作的一大進步。這一制度后被清代承襲,是現代公文“擬辦”程序的發端。
文書行文避諱制度
文書行文避諱制度始于秦始皇。他規定所有的書面文字或口頭語言中,均不得寫出或說出他的名字。秦始皇姓嬴名政,古代“政”通“正”,他稱帝以后,便規定任何場合不準用“正”字,凡需要表達“正”的意思時,一律用“端”字代替,如“正月”要改為“端月”。
文書行文避諱制度為我國歷代襲用,唐朝以后還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。《唐律疏義·職制》第115條規定:“諸上書若奏事,誤犯家廟諱者,杖八十;口誤及余文書誤犯者,笞五十。”唐太宗名叫李世民,文書中就要諱“民”字,而“民”是一個常用字,凡行文中用“民”字者一律以“人”字代之,否則就要治罪。宋代規定需避諱的字竟達50個之多,如為了避宋太祖趙匡胤名字之諱,將“匡”字改成正、輔、規、糾、光、康、王等字,全國吏民如有姓匡者,一律改姓為“王”。
除了以上幾種文書處理制度外,尚有公文保密制度、公文用印制度、辦文時限制度和催辦制度、元代的“照刷、磨勘”制度、公文傳遞制度等,關系到保密、督查、機要交通工作等。
(文章摘自《秘書工作》雜志;作者:楊樹森)
編輯:劉 健 制作:吳 昊
注:本文來源為《秘書工作》雜志及微信號“秘書工作”(mishugongzuo),任何媒介轉載均須注明來源,否則追究法律責任。
| 歡迎關注秘書工作賬號 |
| 更多精彩,盡在《秘書工作》雜志 |

掃一掃在手機打開當前頁
 冀公網安備13010402001751號
冀公網安備13010402001751號
